
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走了
——追忆陈忠实先生
淤 清
我是在4月的最后一天去缅怀先生的,那时原上的花还未到荼蘼的时间,樱桃正红。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却再也不回来了!

我在先生旧居的小院门前的空地上驻足良久,我屏住呼吸,用力的感受先生旧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可是终究什么气息都没有了。两扇红色的铁门紧锁着,像足了人们闭合的嘴巴,一言不发。哦!原来我来晚了。从外地和遥远的异国他乡赶来了许多看望先生的人,和我一样也在院子门外徘徊,他们交谈着先生的过去,说着一些旁听的奇闻异事以及先生在当时的创作当中遇到的热潮冷讽云云,我想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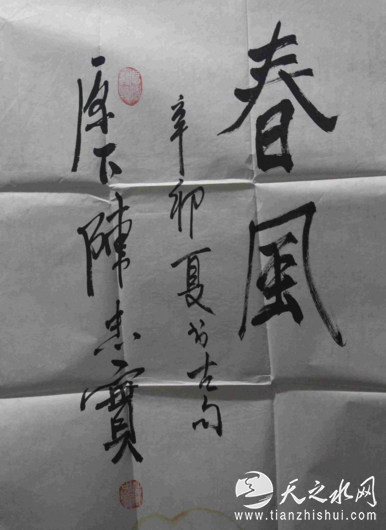
我敬重先生的厚重,敬重先生的作品正如先生的名字忠诚老实,敬重人类最原始的疼痛,敬重乡土,敬重乡村。每当翻开先生的《白鹿原》就像翻开了生我养我的土地,那个距离白鹿原400公里在渭河上游陇东高原一个叫做西坪的地方,它和白鹿原那么的相像。沟沟壑壑,坑坑洼洼、一想起,就颠的疼。先生的《白鹿原》书写了一部渭河平原近半个世纪的变迁,中国乡村命运的多牟但又斑斓多彩,国恨家仇,惊心动魄,这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的秘史,正如他在创作《白鹿原》时写在手稿扉页的那句巴尔扎克的话一样——--------“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无论是《白鹿原》中的乡村权威白嘉轩,还是不守贞洁妇道的田小娥、叛逆的黑娃,我都能在从祖辈哪里听来家乡的故事中找到人物原型,这让我曾经一度十分惊喜,久久不能忘怀,这是中国乡村的共性吧。千百年来中国乡村的进步和封建礼教的碰撞竟然让我把《白鹿原》和西坪联系到了一起。“原上人”和:“西坪人”,陈忠实先生和我,其中的感觉神秘而美妙。《白鹿原》读的我痛感十足,疼痛是人类最原始的记忆,这种记忆来源于乡村,来源于最平凡的生活。
![JS~N%KDSEB`L`M{R]{6CP11](http://upload.tianzhishui.com/2017/0422/1492875861150.png)
先生走了,带着那本垫棺做枕的“砖头”走了。他也许会在人声嘈杂过后的黄昏还会回到生养先生的西蒋村,回到这个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这里有先生的祖辈留下的关帝庙和先生亲手栽种的梧桐树,只要灞河的水一直流着。河川便一直清澈见底。平展的土地上先生精雕细琢的乡村便会一直平实宁静。
![6)2ZWA]E{O2~AZVFMWK$ZTB](http://upload.tianzhishui.com/2017/0422/1492875882193.png)
作者简介:
淤清: 原名汪锋 1993年生于甘肃天水。 自由撰稿人、 天水五点半诗群成员、 中国秦岭诗会会员 、现供职于西安高科学院。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